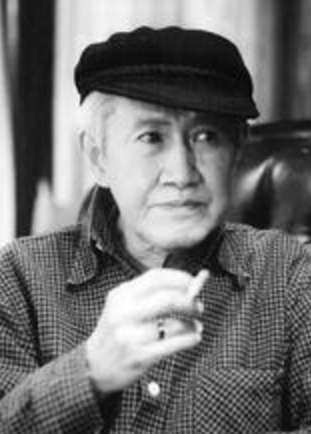尼采有哈姆雷特的一面,也有堂吉诃德的一面,我偏爱他哈姆雷特的一面,常笑他堂吉诃德的一面。现在读尼采看来是太难了——很多人是在读他堂吉诃德的一面。小时候母亲教导我:“人多的地方不要去。”现在想来,意味广大深长,在世界上,在历史中,人多的地方真是不去为妙。”最快乐的梦,不及醒寤的一刻。——纪德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和哲学,小说中一点不肯流露,所谓“冰山是只露八分之一在水面上”。我的童年少年很苦闷,没有心情接受普希金那种典雅的美。倒是爆烈、粗犷的美容易引起共鸣。悲哀痛苦,分上下两个层次,一个是思想的心灵的层次,对宇宙、世界、人类、人性的绝望,另一个是现实的感觉的层次,是对社会、人际、遭遇的绝望。高尔基、鲁迅、罗曼·罗兰,有下面的一个层次,而对上面那个层次(即对宇宙、世界、人类状况、人性本质),未必深思,一旦听到看到共产主义可以解决社会、生活、人际关系、个人命运,就欣欣然以为有救了。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,都是人想了解自己。这仅仅是人的癖好,不是什么崇高的事,是人的自觉、自识、自评。求知欲、好奇心、审美力,是人类最可宝贵的特质——“知”,宇宙是不可知的;“奇”,人以为奇,动物不以为奇;“美”,更是荒唐,梅兰竹菊,猴子毫无反应。人类要自救,只有了解自己、认识他人,求知、好奇、审美,是必要的态度。在世界可知的历史中,最打动我的两颗心,一是耶稣,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尼采感动我的是他的头脑和脾气。契科夫作为一个人,非常有意思。谦和、文静、克制、优雅,通达人情。鲁迅说契科夫的小说是“含泪的微笑”,中学水准。我认为文学不需要含泪,也不需要微笑。艺术是不哭,也不笑的。少年人应有强烈的羡慕,咬牙切齿的妒忌——这样才能使软性的抱负,变成硬性的。象征主义——带有婴儿口吻的苍老的风格。西方一切归于神,中国一切归于自然,我以为两...